

閱讀提示:黃岡麻城77歲的林水珠老太太,含辛茹苦將兒女養大成人,卻不幸于20年前罹患腎癌。在生命與病魔抗爭的日日夜夜,老人堅強不屈、樂觀向上,猶如挺拔在風中的一桿旗幟,激勵后輩笑迎生活、勇往直前。
人生易老,信念不老。眼看一年一度的重陽節就要到來,面對病榻上風燭殘年的白發親娘,兒女們看在眼里,痛在心中。老人的兒子丁安國(國家稅務總局羅田縣稅務局黨委書記、局長)含淚寫下這篇文章,“天之大,唯有你的愛是完美無瑕”,獻給天下殫精竭慮的父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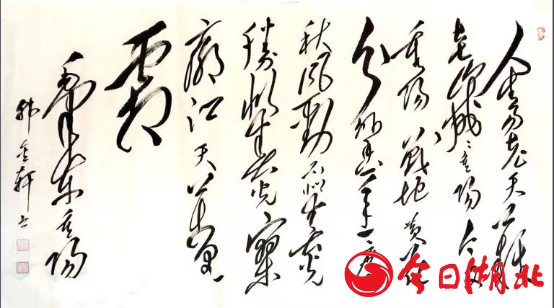
娘,姓林名水珠,1946年2月23日(農歷正月廿二)出生,到今年正月廿二,年滿77歲,雖然還遠未達到我們作為子女、一直心心念念要娘活成百歲老人的預期,但我毅然決然要為娘寫下這些文字,因為我在誠惶誠恐中冥冥感覺到娘的時日不多。
娘,是一片天,又是一粒塵,就像她的名字,偉岸博大到有如浩瀚林海、廣袤無垠,又平凡渺小到恰似林間水珠、轉瞬即逝。有娘健在的日子,習慣于無所顧忌地享受著歲月靜好,怕娘離去的時刻,又不禁無可救藥地回首起過往流年……
娘出生在與我們丁家山對面遙相呼應、八里小山路外的林家山,兄妹6人,上面一個大姐、一個大哥均趙姓,與娘同母異父,生活在趙家,外婆是在趙公去世后改嫁我外公林氏的,在林家,娘的二哥天生肢殘智障,娘下面另有一個弟弟、一個妹妹。我印象中從來沒見過外公,據知他在娘兄弟姐妹幾個還未成年時就去世了,所以在外婆家,其實一直是娘打小就與外婆相依為命,撐起了那個風雨飄搖的家。
娘這一輩子孝老愛親。做姑娘的時候是,嫁為人婦后也是。五十幾年前、上個世紀六十年代中期,娘嫁到了我們丁氏這個很不富裕卻負擔極重的家族。父親兄弟一個,上面一個姐姐、下面三個妹妹。祖上父親的奶奶、我的曾祖母,與我們一家同住在村里塘邊一個石頭大門院內,曾祖母住進門右側,我們家住左側,據父親說自他記事以來印象中從沒見過自己的爺爺,所以曾祖母守寡至少有三十多年,膝下兩兒一女,也就是我的爺爺、叔公、姑奶奶。曾祖母姓胡,有著“三寸金蓮”、小腳伶仃,是一位身材瘦小卻極其聰明智慧、樂觀豁達、勤勞善良的女人,我兒時聽聞過不少關于曾祖母智斗小日本鬼子、與土匪巧妙周旋,從而保全一大家老老小小性命及財產的勵志故事,那時的我特別喜歡爬靠在曾祖母身上、掰弄揉扯她臉上被滄桑歲月刻蝕留下的深溝淺槽,曾祖母總是被逗得呵呵憨笑。記得一次在曾祖母家里正玩耍時,曾祖母突然從所落坐的板凳上向后仰倒在屋旮旯的柴禾上,由于年事已高動彈不得,我也因個小無法扶起她,曾祖母仍然笑容可掬地說:乖乖,快去喊你父(我們對父親的稱呼),幸好同在大院,照應方便。曾祖母也生于1893年,是在唐山大地震、毛主席逝世后第二年溘然長逝的,時年84歲。雖然我當時還是垂髫年華,但當年她老人家慈祥的面容至今回想起來仍歷歷在目。姑奶奶外嫁他鄉后兒女成群、成了大戶人家,所以父親的表親兄弟姐妹特別多。因動輒躲避戰亂、長期蜷縮于潮濕的山洞,叔公(我們尊稱他為“矮二爹”)年紀輕輕時就癱瘓臥床,一輩子未娶,1983年未屆花甲、55歲時就去世了,爺爺在我大姑媽、父親、二姑媽出生后也雙腳癱瘓,后半輩子靠雙手在地上爬行,直到1984年與世長辭,時年66歲。爺爺彌留之際特別盼吃桔子,條件所限硬沒能滿足他老人家的愿望,這是我們心中永遠的痛,爺爺那天堅持等到姐姐寒假歸來才安詳地離開我們。爺爺叔公都非常疼我們,回想起當年對他們偶有不孝順、使喚不耐煩,至今心里還特別難受。爺爺和叔公身殘志堅,都會手藝活兒,特別是爺爺,諱名丁宋川,是遠近聞名的能人、受人敬重的“川叔”,不僅能寫一手剛勁有力、讓人艷羨的毛筆字,能做一手精細的扎掃把兒、竹篾活兒、編織草鞋等以補貼家用,還會用易經的知識卜卦算運,精通六壬預測法,即民間傳說的“打時”,左鄰右舍時有丟了東西的,第一時間求助爺爺“打時”尋物,爺爺往往掐指一算、多有靈驗。爺爺癱瘓后,垸下堂親的一位叔公入贅奶奶家,我們一直習慣于尊稱他為“老爹爹”,與奶奶成婚后生下兩個女兒,即父親后來同母異父的兩個妹妹也就是我的三姑媽、細姑媽。“老爹爹”是一名泥瓦匠,人也特別樸實善良厚道,一輩子寧可自己多吃虧、從不占別人便宜,他在為人家拆陳年老屋時掘出大量銀元,在主人毫不知情下無任何遲疑告知他們,那戶人家特別感激,“老爹爹”甚至曾有著星夜回家路不拾遺、擔心撿了別人丟失的布匹怕人家找不回、動人到“迂”的凄美故事,“老爹爹”一生勤勞、累到佝僂,于1982年67歲時離世。面對老弱病殘,娘眼看這個家,明知擔子千斤重,起初就沒患得患失;娘嫁到這個家,毅然扛起千斤擔,從來就是無怨無悔。幾十年來,她與父親一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那個物質匱乏的年代,通過自己的勤勞雙手經營起一個日益富足的家,不無體面地先后外嫁了我的四位姑媽,侍奉并為包括我外婆在內的六位老人養老送終,還兒女成群。娘一直被親人們津津樂道,族內長輩們常常逢人愛夸“我們家的水伢”,幾個姑媽們往往開口便稱“我們家的水姐”。娘用行動教育兒女要如何孝老愛親。
娘這一輩子聰敏能干。因為自小家境貧寒,娘一輩子沒上過學堂門。但這絲毫沒制約和影響娘的聰敏能干,稼穡耕種、飼養畜牧、紡線織布,娘無所不能。“大集體”年代,因家大口闊,我們家一直是有名的“缺糧戶”,作為家里的主心骨、主勞力,為了養家糊口,父母只能沒日沒夜地掙工分。父親是百分百的“主外”勞動力,每天起早貪黑辛苦勞作,娘卻既要主內、計劃一大家人的吃穿用度,娘總愛說:吃不窮、喝不窮,計劃不到一世窮,除了將全家人居家日子安排的井井有條,娘又要忙外、與父親一道在外打拼,娘的精明“能干”、巾幗不讓須眉是出了名的。正是因為娘和父親的勤勞肯干,即便在那個積貧積弱的年代不僅沒讓一大家人餓過肚子、還生活得很好,更是贏得了左鄰右舍、鄉里鄉親的尊重。70年代中后期,因村前水塘擴建整修需要,塘邊一些住戶包括我們家的石頭門大院在內,面臨著居家搬遷,也因此帶來相應村小組(生產隊)調整問題,我們家原在林家壇生產隊,被后來的蔡家沖生產隊從幾家擬搬遷戶中直接點名邀請入隊,且公開說一概不要其他搬遷戶,理由就是因為娘和父親勤勞善良、每人都要頂幾個勞動力。娘的聰敏能干更體現在改革開放、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以后。1982年我們那里開始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有了自己的田地,如同那個年代中國大多數勤苦農民一樣,娘和父親勤勞致富的熱情更加極大地迸發出來,開啟了戰天斗地其樂無窮的激情歲月。責任田地到戶第一年,我們家光稻谷就收獲了三千多斤,南瓜、紅薯等農副產品堆積成山,僅壓榨花生油就多達120多斤,比在大集體時代幾十年間所分得花生油的總和還要多很多,令十里八鄉都嘖嘖稱奇。記憶中的爺爺一直是一個非常陽光、樂觀豁達的人,記得當時在目睹家里糧食谷物滿倉實囤的豐收景象后,他老人家都禁不住喜極而泣:冇想到現如今恁幸福。娘的能干不僅體現在不輸男人的稼穡耕種農活兒上,更體現在飼養畜牧、紡線織布等方方面面。那個時候,我們家年年雞鴨鵝成群、豬牛羊滿圈,特別是娘飼養的母豬下的豬崽特別搶手,一個個圓圓滾滾、特別可愛,常常被買家戲稱為“小獅子”。娘養蠶技術一流,每年所產蠶繭色澤雪白純正、品質厚實均勻,似乎總是能有別于其他人家賣出個上等的好價錢。娘還特別擅長紡線織布,從搓棉成捻、抽絲成錠、機織成布、染色成品一整套流程,娘都游刃有余有若行云流水。穿上娘織的棉布衣褲、墊蓋上娘做的大布被單被套,未必光鮮卻有著獨特的貼身舒適感。我們兄弟姐妹四個至今都珍藏著娘為我們留下的印花大布被單被套。
娘這一輩子厚德致遠。也許是因為自小就歷經風雨坎坷、飽嘗了酸甜苦辣,也許是恰逢年富力強趕上改革開放、享受了改開富民的幸福甜頭,更或是因為娘本身就有著根植于心的純樸、善良、厚道,所以娘特別感恩黨、感恩政府、感恩這個偉大的時代、感恩那些困難時期接濟幫助過我們家的人。在家境日益殷實、日臻富庶后,娘常常由衷地感嘆:沒有國家的好政策,哪有現在的好生活,做夢都想不到我們家能有今天……娘講不出愛黨愛國的大道理和豪言壯語,但娘自兒女們小的時候就口口聲聲常叨要愛黨愛國、做對國家有用的人。娘目不識丁卻特別看重那些有知識有文化的人,家里也結識了不少公社、鄉里甚至縣(市)里有頭有臉的“國家干部”,記憶中兒時來家里吃住的,時常不乏穿著時髦、談吐不俗的客人。娘不懂“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的傳統經典文化,卻在以最樸實的方式言傳身教育兒女。即便是物質越來越富足、日子越來越好,娘也從沒被“小富即安”的小農思想禁錮,始終篤信“讀書是唯一的出路”,所以執意要培養兒女讀書,立志成為“吃國家飯的人”,娘也從來不重男輕女,手心手背、兄弟姐妹幾個都是娘的心頭肉。姐姐從小天生麗質、天資聰穎,一直是兄弟姊妹幾個的驕傲,是我們這個家族里親外戚的榜樣,也是當年村里甚至十里八鄉津津樂道的“鄰家的孩子”。姐姐那茬兒,包括到后來我上學后也一樣,村里從小學到初中分別與我們姐弟一起上學的同學剛開始共一二十人,后來因方方面面原因逐年減少,幾乎很少有能考上高中的,但在極力鼓勵支持兒女們一路求學上,娘的心始終堅如磐石。姐姐從小學到高中成績常常名列前茅,所以一直非常被學校看好,這也讓娘和父親甚為欣慰,終于在1984年高考中不負厚望取得理想成績。姐姐本可選擇一所理想的大學,但為減輕娘和父親的負擔,特地填報了一所當地著名的全日制兩年的中等專科學校,成為恢復高考以來村里第一個靠讀書走出農村的女孩兒。在校期間,姐姐一直擔任學生會干部,兩年后遵照個人意愿直接被優先分配進稅務部門工作。參加工作后,諸如“全國稅務系統稽查能手”、“全國稅務系統征管能手”等等,姐姐榮譽滿身,這也特別讓父母及弟妹們長臉。只要兒女有出息,娘和父親再苦再累也甘之如飴。總記得我上小學第一次領回獎狀,娘遠遠瞧見就喜出望外,那高興勁兒我永生難忘,娘當天還特地用兩個土雞蛋炒米飯算是獎賞我,那是一輩子銘刻于心的味道。高考后我也學姐姐,主動放棄了上大學的機會,而是填報了許多學子夢寐以求的、全日制兩年后即可包分的湖北省稅務學校,收到錄取通知書后,娘樂得一夜未寐。為不拖累父母,我不顧家鄉習俗執意不讓家里舉辦升學宴,第一次走出大山赴省城上學那天,娘獨自在家門口燃起長長一串鞭炮、佇立大門前目送兒遠行。在娘和父親苦心經營、悉心培育下,兄弟姐妹四個陸陸續續都有了自己理想的工作、事業和幸福家庭。
娘這一輩子勤儉節約。娘總是跟兒女們講: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娘自己也是一個十分好勝要強的人,似乎對于任何事情,要做就要做最好、要爭就要爭第一。剛剛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擬分田分地到各家各戶時,村里很多家庭不愿分得那些預定產量太高的田地,以希望分到更大面積的田地、從而能產出更多的糧食。娘和父親主動認領了那些別人家不要的高產田地,哪怕田地分得少一些,但娘和父親堅信:事在人為,只要人勤地不懶、定會秋后糧滿倉。事實的情況真的是這樣,與同樣人口規模的家庭比、甚至與垸里很多大家庭比,印象中我們家每年的糧食、作物特別是油料作物、農副產品都比別人家多。當時村里有人不無疑問還少有微詞:真有些想不通哈,進文叔家里那么多人要吃飯,家里勞力又不多,他們家么總奔的那么快活。父親說鄰居家的耿伯是這樣回應那人的:這有什么想不通的,人家是么樣吃苦的曉得嗎,你哪天起個大早去他們家窗外看看就知道,進文叔哪天不是天還冇亮就去田地里干活了?他們家水嬸哪天不是從早到晚就在家里喂啊養的、紡啊織的?無論是日子清貧還是后來日益富足,娘一直非常節儉,一粥一飯絕對不浪費、半絲半縷也彌足珍貴。娘的節儉體現在,日子再苦也好、年頭好了也罷,娘都能將家計安排籌劃得有滋有味、如詩似畫,秋收后作物秸稈、穿舊的破衣濫衫、好心人接濟的物什,娘都能魔法般地變廢為寶。娘重節儉卻十分厚愛著自己的親人。父親作為家里的頂梁住,娘對父親的體貼關照無微不至。印象中,每天早上新鮮豬油加白糖、開水沖泡土雞蛋一直是父親的早餐標配,什么有營養補什么,所以父親身體一直硬朗,即便是現在年過八旬依然健步如飛。娘重節儉,卻一直不讓兒女在吃穿用度上寒磣。70年代后期姐姐外出上初中、高中后,每個周末回來全家人都能飽餐一頓燉豬肉。實行責任制物質更加豐富后,家里更是香噴噴的油條、油餅等各種美食不斷。每年春節,娘都會讓兒女們穿上用最時興的布料所量身定做的新衣服、拉底兒布鞋,走到哪里熟悉的人們常愛說“這是水姐家的伢”,這讓兒女們走家串戶、走親訪友拜年時特別地自信、特別有底氣。娘以節儉言傳身教著兒女。娘為兒上的人生第一課讓我沒齒難忘。還是在大集體時,那一年花生成熟后,生產隊里炒了一大竹筐花生,在分吃前我為妹妹在筐里上面小心翼翼拿了兩顆炒糊的花生,當時就有人指責讓我哭了鼻子,娘知道后心疼不已,首先給在場所有人上了一課:小孩子不懂事好吃,也就拿了兩顆炒糊的花生,你們么犯的著這樣傷孩子的自尊心啊,全場鴉雀無聲。娘說完摟著我痛哭流涕:兒啊,記住娘的話,別人家的東西特別是公家的東西,一定不能隨便拿,我似懂非懂地抱著娘淚如雨下,那一年我不到7歲。在兒女們參加工作成為“吃國家飯的人”后,娘講不出諸如“廉潔奉公”、“潔身自好”的大道理,卻時不時叮囑兒女決不可以貪占公家的一分一厘。娘的節儉更體現在大方于人刻薄于己。我參加高考那年,娘走了幾十里的山路去賣蠶繭,路遇高考拿分歸家的同學,娘試探著問他們:你們也是參加高考的學生唄,認不認識我們家的安國哈?也不曉得我安國考的么樣?當我的同學說:認識認識,丁安國是我們的同學,他考的不錯,這次肯定走了(意思是能入學深造),娘聽到這里,平生第一次為自己奢侈了一回,花兩毛錢連買了兩瓶汽水犒勞自己。

娘這一輩子樂善好施。娘不僅孝老愛親、厚愛自己的家人,娘一輩子樂善好施。日子再苦再累、尤其是在日子越來越好有能力幫助別人后,娘常常接濟那些窮苦的人家。記憶中,在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后,每年年關,村里村外來家里借米借糧的不在少數,娘總是慷慨解囊,事后不管人家有沒有能力歸還,娘從不催還。娘一輩子愛干凈,總是將家里拾掇得一塵不染,那年頭來村里辦事的客人特別喜歡吃住在我家。父親天生一副好嗓子,是村里戲班男扮女裝的當家花旦,戲班的教練姓李,是一名專業的戲劇演員,我們都隨大人叫他“李師傅”,每次來村里指導戲班時,“李師傅”只選擇來我家,一住就是一兩個月甚至半年。改革開放讓大多數國人思想來了一次大解放,那年代行商坐賈特別多,時常有“貨郞擔”來村里賣貨,娘憐憫人家的辛苦,時常免費地給他們供吃供喝。新洲的一位王阿姨每年秋冬天來我們村推銷毛線,娘不圖她一分一毫好處每次讓她吃住在我家,那位王阿姨特別感激娘,后來領一家老少專門來我家感恩娘的善良厚道。娘的樂善好施讓我們家結識了不少窮親戚,主動與我們家結成干親,直到現在那些娘資助過的人家始終念叨著我們家的好。娘的樂善好施還體現在尊師重教上,娘每年要為兒女所在的村辦小學捐款捐物,還時常請村小、初中、高中的老師來家里吃飯。娘的樂善好施讓兒女們懂得應該如何去同情弱者、如何去扶危濟困。2018年,我帶年幼的兒子去黃岡市婦幼保健院早教中心參加一個親子活動,讓我第一次見證了觸及靈魂的一幕:那是一家四口,蘄春縣大同鎮葛山村人,父親袁知江肢殘只有一只手,母親雙腳癱瘓靠輪椅行走,一雙兒女一個靠雙拐支撐走路,一個靠一張木板凳在地上爬行,即便這樣,那雙可愛的兒女始終表現得特別陽光、特別樂觀。經詢問得知,他們家是帶孩子來早教中心做康復訓練的,雖然一雙兒女都是先天肢殘即便做康復訓練也幾乎起不了任何效果,但看的出來他們一家渴望過正常人生活的愿望十分強烈,這讓人萬分感慨。從那以后,我要了孩子他爸老袁的微信和電話,決定盡己所能去幫助這個苦命的一家、不離不棄。幾年來,除錢物資助外,還力所能及幫助解決了他們家住房修繕、兒女上學等諸多問題,特別是費盡周折、通過協調方方面面關系解決了一家四口殘疾證升級問題,使全家每月殘疾補助大幅上升,從而讓一家人生活上沒了后顧之憂,這讓我深感欣慰。他們家也一直以一種最樸實厚道的方式回饋我,毫無芥蒂把我當成家里一分子,喜事樂與我分享、難事愿向我傾訴。后來,當我把這件事情告訴娘后,娘樂不可支像個孩子:我兒好樣的,懂得同情可憐人,懂得幫助別人家。
椿萱并茂的日子寧靜祥和、讓人特別幸福。最愜意的莫過于,工作在娘身邊時,“晨則省、昏則定,出必告、反必面”,能每天去看望父母,哪怕自己也已年過半百,依舊能嗲聲奶氣似兒時、拉長一聲:娘哎,我來了……娘也照例回一聲:來呀,我的命,陪伴著娘和父親、擠坐在父母中間,享受著娘的輕撫和愛憐,青春了歲月、溫暖了時光。溫馨的日子又特別容易麻醉人的靈魂。常言道來日方長,來日又何曾方長啊。疫情肆虐最嚴峻的時候,娘和父親都挺過來了,這讓我們做兒女的特別欣慰,但第二波疫情過后,娘慢慢不能自理,只能坐上了輪椅。娘特別愛聽兒為她唱歌,最喜聽的曲目是《兒行千里》、《拉住媽媽的手》、《疼愛媽媽》,“兒行千里揪著媽媽的心頭肉……千里的路啊,我還一步沒走,就看見淚水在媽媽眼里、媽媽眼里流……媽媽眼里流……”,每次聽兒唱歌,娘都神情專注,特別是在身體每況愈下后,娘還會聽到老淚縱橫。“媽媽的腰也彎了,媽媽她白了頭,受苦受累的媽媽喲,我要背著你走……”,8月20日,我平生真的第一次背了娘。頭一天是周六,娘在父親和兒女們攙扶下一起回到老家麻城,參加了我侄子的升學宴,當天即返回黃州。妻子好心,提議就周末時間索性接娘和父親及姐妹們來我們家小聚、一起吃個飯,大家欣然同意。那天,我從樓上背下娘,小心翼翼抱上車,并帶上輪椅,接娘到我所在的小區,在院內轉轉看看,去家里吃了午飯。誰曾想,正是因為我平生的那第一次背娘,造成了娘的病理性骨折,娘已脆弱到一個小小的外力就能給她帶來無可挽回的傷痛。“長大了以后,還拉著媽媽的手,想起兒時的不孝順,我心里好難受……”,周末陪護在娘身邊,病床上的娘一刻不松地拉著兒的手,我平生第一次這么長時間端詳和感受了娘那雙飽經滄桑而又特別溫暖的小手。我照常壓低嗓門為娘唱起了歌,娘到后來一反常態打斷了兒:莫唱了,娘心里好難受……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奪眶而出的淚水……愿上天保佑我娘平平安安!
娘,下輩子您還做我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