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身處江漢平原懷抱的荊州,成就“魚米之鄉、天下糧倉”的美譽,如今再次擔負起“建設江漢平原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示范區”的歷史重任。
推動鄉村振興,農村基層黨組織建設是關鍵。
紅色會堂聚攏人心、紅色頭雁振翅領航、新型村級集體經濟激活發展動能……在“紅色引擎”驅動下,荊州千里沃野之上,處處涌動實干熱潮,鄉村振興的美麗畫卷徐徐鋪展。

“紅色陣地”迸發強勁活力
早上,江陵縣資市鎮先進村村黨支部主題黨日活動正在舉行。
新建的黨員群眾活動室內,主背景墻上,一面黨徽懸掛在正中央熠熠生輝,左右兩側各放置5面紅旗,其他墻面懸掛著領袖經典語錄、黨組織網絡圖、黨員群像圖、崗位職責、榮譽欄等。置身其中,頓感莊重。
“我志愿加入中國共產黨,擁護黨的綱領,遵守黨的章程……”村黨總支書記王金龍佩戴黨徽,舉起右拳帶領與會黨員一起宣誓,重溫入黨宣誓時的莊嚴承諾和堅定決心。
會場內,錚錚誓言激蕩回響,讓人心潮澎湃。
“不一樣,真是不一樣,以前哪有這種氛圍!”老黨員吳傳祥感嘆不已:“村里最困難的時候,黨員連開會地方都沒有,一個小會議室,里面坐一半,外面站一半,吵吵嚷嚷,沒多大一會就散場了。”
“如今,這里不僅聚集了人氣,更聚攏了人心,村里的理論宣講、農技培訓、民俗展示、鄉風評議等活動都在這里舉行,村民們的精神文化生活‘活’起來了,咱們要對村‘兩委’點個贊。”吳傳祥向記者豎起大拇指。
這些改變,源于荊州市正在深入推進的農村“紅色陣地”建設。去年來,荊州市委提出,把農村黨員群眾服務中心打造成農村“紅色陣地”,把村黨組織建成堅強的“戰斗堡壘”,推動基層黨組織建設全面進步全面過硬。
建起來——按照"1+5+X"模式規范化建設“紅色陣地”,"1"即把黨員活動室建設成“紅色會堂”;"5"即完善便民服務、衛生服務、商貿服務、文體活動、公共服務等功能建設;"x"即有條件的村,可因地制宜建設鄉風文明禮堂、鄉賢名人館等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場所。
用起來——把“紅色陣地”建成“五個中心”,即旗幟鮮明講政治的黨務中心、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推進中心、引領鄉風文明的文化中心、凝心聚氣的信息中心、便民利民的服務中心。
建與用,“紅色陣地”如星星之火,在全市各地呈燎原之勢。
“今天我們播報精準扶貧政策,給大家講一講貧困戶脫貧出列標準……”荊州區馬山鎮鳳林村九組村民鄭高蓮邊干著農活邊聽著廣播。
“從傳遞黨的聲音,到宣傳黨的政策,再到播報種養信息,小小的廣播,把鄉親們的心拉得更近了。”鳳林村村黨支部書記佘友林說。
如今,這樣的小廣播已成為全市各村“紅色陣地”建設的標配。通過推動村級廣播“村村響”“天天講”,不僅為鄉村治理提供了便利,還拉近了黨和群眾的心,在廣大群眾中營造出聽黨話、感黨恩、跟黨走的強大氣場。
“紅色陣地”上,不僅有飛揚的“廣播聲”,還有各種“接地氣”的主題活動,讓村民們的精神文化生活“亮堂”起來。
去年12月8日,石首市團山寺鎮過脈嶺村熱鬧非凡,周邊十里八鄉的村民在此參加傳統民俗文化活動“糍粑節”,眾人揮動木棒齊搗紫糯米,慶祝鴨蛙稻米豐收。
“我們趕上了好時代!”說起家鄉建設,村民臉上溢滿著幸福的笑容。
近兩年來,石首市各村依托“紅色陣地”打造鄉村文體活動大舞臺,持續開展“快樂廣場舞大家跳”“紅色文藝輕騎兵”、送電影下鄉等活動,類似過脈嶺村“糍粑節”這樣的活動,更讓“紅色陣地”成為展現傳統文化強大魅力的重要載體。
東風夜放花千樹,最能致遠是書香。江陵縣白馬寺鎮黃淡村,將農家書屋建設與精神文明創建相結合,不斷推陳出新,開展豐富多彩的讀書活動,獲評“全國示范農家書屋”,這是荊州市唯一獲此殊榮的農家書屋。
松滋市劉家場鎮三堰淌村依托“紅色陣地”,每年開展“好婆婆”“好媳婦”“好兒女”和“十佳文明村民”評選活動,還制訂了《三堰淌村村規民約》,成立村紅白理事會,積極倡導推行移風易俗和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
炎炎夏日,各地“紅色陣地”建設仍如火如荼。截至目前,全市共投入資金18億余元,建設達標率達98.2%。“紅色陣地”重塑基層黨組織組織力,重新讓群眾“圍著集體轉、跟著集體干”,為鄉村振興集聚了無窮力量。
“頭雁領航”帶動“群雁齊飛”
鄉村振興,關鍵在人,關鍵在黨組織帶頭人。這就迫切需要“頭雁領航”,扛起新的使命。
41%的村黨支部書記年齡50歲以上,51%的村“兩委”干部學歷在初中及以下……這是去年江陵縣村“兩委”換屆前的基本情況。
去年4月,江陵縣面向社會公開選聘村黨組織書記,身份不限,籍貫不限,但要求年齡在45周歲以下,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黨齡3年以上。
誰說農村不吸引人?10個名額,67人報名。經過嚴格選拔,最終確定10名村黨組織書記人選,被派往10個村支書空缺或年齡過大退下來的村。
外來的和尚真的會念經嗎?村民們拭目以待。
在馬家寨鄉萬場村,每畝11元灌溉水費成了“攔路虎”,由于村集體經濟薄弱,這筆費用由村民自費。2016年以來,班子不力,沒能收齊費用,這事就一拖再拖。
選聘村黨組織書記李德透到任時,正值抗旱關鍵時期,為保障正常灌溉,不激發村集體矛盾,他墊付了全村灌溉水費3.6萬元。8月,他又爭取到扶貧專項資金用于發展食用菌項目,流轉土地35畝,既能讓村民收益,又能為集體增收,2018年萬場村集體經濟收入達到9.23萬元。
這并非孤例。秦市鄉秦家場村的肖海,解決了持續十幾年的廢品收購站占道經營問題;白馬寺鎮曲垸村的楊長波,聚焦處理村級公墓改建問題,得到群眾高度認可;普濟鎮趙家嶺村陳克超,協調解決201戶村民的自來水改造問題……
看得見的變化,觸手可及的實惠,讓這批選聘的村干部得到了村民的真心認可。
在去年的換屆選舉中,荊州堅決將那些“守攤子”的“維持會長”換下來,全市村黨組織書記調整721人,調整面高達48.29%;45歲以下462人,占31%;“派”和“聘”共308人,占20.6%。
數字變化的背后,是荊州市委強力推進農村改革的決心。
“近年來,隨著農村經濟和社會結構變化,荊州農村‘非農化’‘空心化’程度加深,直接導致了‘空殼村’‘薄弱村’的出現,而這些村莊普遍存在缺資源、缺人才、缺資金、缺發展條件等問題。”荊州市委組織部有關負責人介紹說。
近年來,荊州市委在全市農村范圍內推行合村并組,讓空殼村、薄弱村抱團取暖、捆綁發展,促進農村資源優化配置。目前,全市共有行政村1495個,比調整前2262個村減少了767個,減幅為34%,極大增強了村組干部戰斗力,有力促進了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
有了堅強的戰斗堡壘,今年初,荊州大力開展“帶頭投身鄉村振興,帶領群眾共同致富”活動,吹響了全市農村黨員奮戰鄉村振興第一線的號角。
監利縣新溝鎮雷河村黨員張才艷,是村里有名的“致富能手”。這些年,他先后成立監利縣橫新牲豬養殖專業合作社和橫隆水稻種植專業合作社,廣泛吸納貧困戶就業。
困難戶張立榮因病喪失勞動力,無法從事農業生產。張才艷主動上門溝通,將老人家里22畝地以免費托管方式,交由橫隆水稻種植專業合作社全程管理,對張立榮老人給予分紅。
洪湖市烏林鎮吳王廟村是遠近聞名的貧困村,從2010年到2019年,荊州市人民檢察院正縣級調研員、村黨支部第一書記陳雪飛深深扎根于此。
9年風雨兼程,9年駐村惠民,陳雪飛結上52戶“窮親戚”,修橋鋪路、通水通電、防汛抗旱、培育產業、建設美麗鄉村,吳王廟由落后村變成了先進村。
“現在,我們這里有氣派的文化廣場和詩詞長廊,有斥資60萬元建成的老人兒童中心,還有櫻花漫天的人民樂園。”村黨支部書記余光寶自豪地說。
一個支部就是一個堡壘,一名黨員就是一面旗幟。從村黨支部書記李德透,到駐村第一書記陳雪飛,再到致富能手張才艷……荊州廣袤的田野上,正繪出“頭雁領航”帶動“群雁齊飛”的生動畫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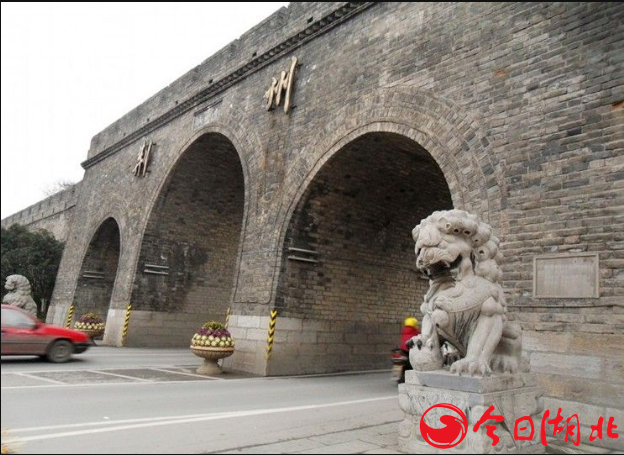
支部引領激活鄉村發展動能
“前幾天,我們開村民代表會,通知了90人,沒想到來了近200人,坐的地方都沒有。”公安縣獅子口鎮義星村黨支部書記黃云才感慨:“以前開個會,求都求不來。現在,村里爹爹婆婆一聽說要開會,麻將一推都來了,生怕錯過什么好事。”
的確有好事。就在當天,義星村結了上半年的“勞務賬”,加入村勞務合作社的村民,總計領到了150余萬元工資。
從“百呼一應”到“一呼百應”,變化的背后,是公安縣將“紅色陣地”作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推進中心,大力開展以村為單位的“三個合作社”建設(即土地股份、勞務、資本合作社),把千萬個小農戶聚攏來,加快實現鄉村振興。
村民蘇祥兵家情況特殊,他和妻子唐貴蓮身體都不好,不能從事重體力活。不過,義星勞務合作社給他們在凌云家庭農場派了一份合適的工作。蘇祥兵騎三輪車,運送農資,一天120元。唐貴蓮從事除草、剪枝等輕農活,一天90元。
蘇祥兵夫妻倆有多重身份,家里的9畝地入股義星土地股份合作社,他們是土地股份合作社的股東;夫妻倆都加入了義星勞務合作社,他們是勞務合作社的員工;他們還現金入股村里的資本合作社,成為現代農業的“合伙人”。
“三個合作社”最突出特點是堅持村社合一,村黨支部創建領辦、村集體占有股份、村支書兼任合作社理事長成為標配,不僅充分發揮村集體自治組織和經濟組織的雙重屬性,還有效解決基層黨組織凝聚力、組織力、戰斗力不足的問題。
記者走訪發現,“三個合作社”模式實施后,村民們普遍可以拿到“四金”:流轉土地掙租金、入股分紅得股金、參與勞務拿薪金和農閑時在外打零工賺現金。
有了公安縣“三個合作社”探路前行,今年5月,荊州市委黨建工作領導小組發出“加快發展壯大新型村級集體經濟”的動員令。
各地摩拳擦掌、躍躍欲試,這種“支部領辦、村社合一、多元合作”的新型村級集體經濟發展模式在全市遍地開花。目前,全市共有村級合作經濟組織673個,有573個村級合作經濟組織的負責人由村主職干部擔任,占比達85.1%。
多年前,石首市東升鎮范興垸村村集體一度虧空達110余萬元。
村委會一班人反復商量,想到了一個妙招:將村里責任田與溝渠及村道之間的零散邊緣土地全部回收管理,栽上數萬棵意楊樹。
村里以前種樹,但成不了材。“在路邊溝邊種樹,村民認為會影響農作物采光,樹還沒長大,就想方設法給弄死。”他們又創新思路,讓村“兩委”與村民簽訂協議,樹木成材售賣后,雙方“三七分成”。
問題迎刃而解。去年,范興垸村“十年育樹”之計迎來第一個驗收節點,賣出了近萬棵樹木,獲得集體收入70余萬元。
與此同時,該村還通過挖掘土地資源、入股專業合作社等方式,不斷增強村級造血功能。去年底,該村村集體賬面資金突破1000萬元。
一花引來萬花開。范興垸村的發展模式在該市復制推廣,催生出“石首富集體現象”。
在江陵縣,各村積極發展聯村集體經濟產業園,探索出了一條“以強帶弱、抱團取暖、共同發力”的聯村發展模式,建成了2個聯村產業發展基地。
該縣整合項目資金680萬元,在馬家寨鄉楊淵村發展占地20余畝的光伏產業,每年可為17個貧困村各帶來3萬元以上的收入;整合項目資金480萬元,在熊河鎮熊河村發展占地800畝的吊瓜產業,每年可為25個經濟薄弱村、軟弱渙散村各帶來5萬元以上的收入。
沙市區立新街道荊江村積極推進集體經濟與個體民營經濟融合發展,2018年,與藍特集團合力規劃促進藍特陶瓷城做大做強。同時,通過以房抵資的形式盤活存量,收回295平方米萬達寫字樓、270平方米學府街坊商鋪等資產對外出租,年收入不斷提高,進一步鞏固了集體經濟發展。
黨建引領,跑出鄉村振興的“加速度”。截至目前,全市集體經濟收入過5萬元的村有1464個,占97.93%。其中,荊州區、沙市區、石首市3地所有村均有穩定的集體經濟收入。(記者吳杰 李天然 通訊員靳祖軒)









